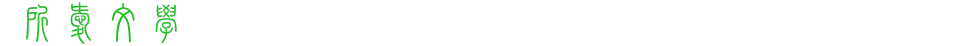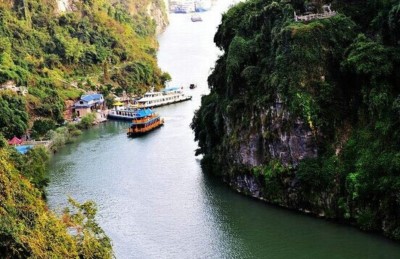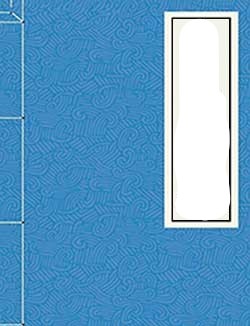夜读散文|《暖冬》
2025-11-17 20:34 编辑:云彩间

西安的午后,总是慢的。我踱上城墙,脚下的青砖被稀薄的日光晒出些许暖意,像是老人手心里攥久了的一塊溫玉。今年的冬,確是不同了。护城河的水并未完全封住,风过时,能听见冰碴子与流水私语的碎响,泠泠的,不那么刺耳。回民街那头,白蒙蒙的蒸汽扶摇而上,羊肉的膻香、甑糕的甜糯,全都搅在這片暖霧裡,將三九寒天熏得一派慈眉善目。這光,是斜斜地打过来的,没什么力气,却足夠將人的影子拉得老長,仿佛時間也跟著變得慵懶而寬裕。空氣裡嗅不到那種乾冷尖利的鋒芒,只有一種渾濁的、近乎宽容的溫吞。这冬日的底子,竟是暖的。
这暖意,自有其来处。
先是那自然之暖,承接着这稀罕的天时。兴庆宫公园的湖边,几株老柳竟還殘著些許頑固的綠意,雖已憔悴,到底不曾徹底枯敗。幾隻麻雀在枯草地上跳躍,啾啾著,全無畏寒之態,胖乎乎的身子像些會滾動的絨球。而那輪冬陽,才是真正的主角。我倚著大雁塔廣場的欄杆,看那光影如一個從容的畫師,一寸寸地,將飛簷、斗拱、石獸的輪廓一一描金。那光移到遊人的背上,便將厚重的冬衣熨貼出一片舒坦的暖,直透肌骨。這光是歷史的,它今日照著我,千年前,也曾同樣地照著那些雕刻塔身的工匠,他們的汗滴與祈願,想必也曾被這般溫暖過。
由此,便自然而然地轉向了那人文之暖。這暖,是西安這座古城積澱千年的體溫。我將手心貼上一塊城磚,粗糙,卻不冰冷。它白日裡吸收了足夠的日光,此刻正從內裡,絲絲縷縷地釋放出一種敦厚的餘溫。這暖意,讓人無端地想起「長安」二字,想起爐火,想起詩篇,想起萬國來朝時,使者袍袖間攜帶的、來自遠方的暖風。這是一種被時間熬煮得愈發醇厚的暖。
再轉入市井街巷,那暖意便更為具體、可親了。小巷口的烤紅薯攤子,鐵桶裡燃著殷紅的炭火,老大爺用鐵夾夾出一個,燙手地遞來。掰開了,那股焦甜的热氣“噗”地一下迎面而來,吃在嘴裡,是近乎奢侈的滿足。或是鑽進一家老字號,捧一碗羊肉泡饃。碩大的海碗像個小太陽,熱騰騰的蒸汽氤氳了眉眼,濃白的湯,爛熟的肉,連同掰碎的饃,一起落進肚裡,於是,一股扎實的、由內而外的暖流,便從胃裡彌漫開來,貫通全身,將一切寒意驅逐出境。
而最動人的,往往是那些不期而遇的人情之暖。城牆根下,一位拉著胡琴的老人,閉著眼,搖頭晃腦地拉著一曲《二泉映月》,那樂聲在暖冬的空氣裡,少了幾分淒清,多了幾分平靜的敘事。旁邊書店的年輕店主,對進出的每一位老街坊都點頭笑笑,道一聲“天冷,裡頭坐”。這份暖,不轟轟烈烈,只是人與人之間最樸素的那點念記與善意,卻如暗夜中的微光,雖小,卻足以照亮彼此的一隅天地。
夜幕將垂,我站在鐘樓之下,看車流水一般滑過,車燈匯成一條溫暖的河流。方才所歷的種種暖意,此刻都匯聚到心頭來,沉靜地盤踞著。我忽然明了,這“暖冬”之暖,並非盛夏那般奔放熱烈的情感,它更像是一種寬容,是嚴酷季節偶爾展現的溫柔側臉。它讓匆忙的步履得以放緩,讓緊繃的心靈尋得一隅舒展。它教人懂得,溫暖並非全然依賴於天時,更多是源於內心對生活的細緻體察與熱愛。
這份暖,是街巷裡市井煙火的饋贈,是歷史深處文明餘燼的溫度,更是陌生人眼中一瞥善意的交匯。它讓這座千年古城,在歲月的寒流中,始終保有著一副不曾冷卻的心腸。這暖冬,於西安而言,原不過是那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火,從未熄滅的,一個溫婉的證明。
查看更多>>上一篇:晨读散文 | 立冬过后就是... 下一篇:夜读散文 | 故乡的冬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