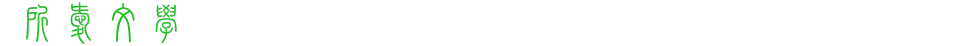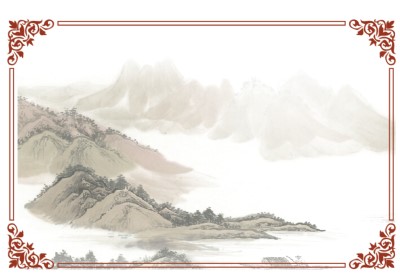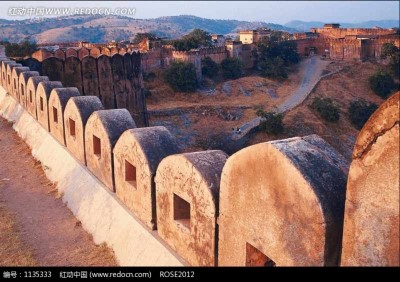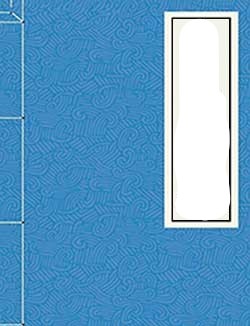夜读散文 | 故乡的冬日
2025-11-17 20:36 编辑:云彩间

我总以为,冬天的魂,在南方是另一样的。它不似北国那样,用铺天盖地的雪,用凛冽如刀的风,来宣示自己的主权。南方的冬,是矜持的,是内向的。它来得悄无声息,像一滴极浓的墨,滴入清水中,不急于散开,只是那么幽幽地、缓缓地,晕染出一片洇润而清冷的底子来。这底子,便是我记忆中故乡的冬日了。
离家愈久,这景致在脑中便愈发清晰,带着一种潮湿的、拂之不去的凉意。
清晨常常是从一场弥天的大雾开始的。那雾不是一缕一缕的,而是一团一团的,厚重、粘稠,仿佛是从天上垂下来的、洗旧了的灰白棉絮,将整个天地都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。远处的山,近处的树,都失了形踪,只剩下些朦朦胧胧的影子,像是用极淡的墨在宣纸上随意抹出的几笔。世界陡然变小了,小得只剩下眼前一方。走在雾里,头发上、眉毛上,不一会儿便会凝结起一层细密的水珠,亮晶晶的。空气吸到肺里,是清冽而甘甜的,带着泥土与草木腐烂后混合的特有的气息。这气息,是故乡冬天的签名。
太阳是稀客。即便来了,也是懒洋洋的,有气无力的,像一个贫血的少女苍白的面庞。它的光,穿不透那浓雾,只在雾的背面,形成一个模糊的、乳白色的光晕,算是给这灰色世界的一点怜悯的慰藉。更多的时候,天是整日整日地阴着的,是一种匀净的、鸭蛋青似的颜色。云层压得低低的,仿佛一伸手便能扯下一块来,拧出冰凉的汁水。
真正的寒冷,是从这无处不在的湿润里生发出来的。那不是干冷的、爽利的寒,而是一种“浸”入骨髓的冷。它无孔不入,顺着你的衣领、袖口,丝丝缕缕地钻进来,贴着你的皮肤,慢条斯理地汲取你身上那一点点可怜的热气。坐在屋里,若不生一盆炭火,那冷气便仿佛能从灰砖的地面、白粉的墙壁里一丝丝地渗出来,聚在屋中,久而不散。这时候,若能捧一杯烫手的浓茶,看那白蒙蒙的水汽氤氲着上升,便觉得是人生顶大的幸福了。
然而,这清寒里,也自有一番倔强的生意。田里的冬麦,伏着身子,叶缘上凝着霜,绿得愈发沉郁。溪水瘦了,流得慢了,却愈加清澈,看得见底下圆圆的、光滑的卵石,石上覆着深绿色的、丝绒般的青苔。最动人的是那水边、桥下的薄冰。薄得像玻璃,指甲轻轻一划,便“喀”的一声,裂开细密的纹路,碎成许多晶莹的碎片,在瘦弱的日光下,闪着碎银子似的光。
这些景,是安静的,内敛的,不喧哗,也不张扬。它们只是那样静静地存在着,像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,所有的颜色都褪尽了火气,只剩下墨的浓淡与干湿,构成一种和谐而寂寞的意境。如今在都市里,冬天只剩下空调外机单调的轰鸣与玻璃窗上模糊的水汽,这种属于自然的、细腻的冬日肌理,便愈发地叫人怀念了。
童年的冬日,却是另一番光景。记忆里的冬天,底色虽是清冷的,却总点缀着许多活泼泼的、暖烘烘的亮色。那时的光阴,仿佛也流得格外的慢。
最盛大的事,莫过于“打年糕”了。那总是在腊月里,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——其实也算不得多晴,只是天色稍开朗些。几户相熟的人家凑在一起,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,支起那巨大的石臼和木甑。壮硕的男人们围着石臼,手里握着光滑的木槌,喊着号子,你一槌,我一槌地,捶打着甑子里蒸熟的、滚烫的糯米。那“砰、砰”的声响,沉实而有力,像是大地沉稳的心跳。腾腾的热气混着米香,在这清冷的空气里弥漫开来,织成一片香味的、暖味的云。我们这些孩子,就在这云雾里钻来钻去,小脸冻得通红,鼻尖上挂着清涕,眼睛却亮得如寒夜的星子。总能在最后,分得一小块刚刚捶打好的、热乎乎、软糯糯的年糕,顾不得烫手,忙不迭地塞进嘴里,那股纯粹的、原始的米粮的甘甜,便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去。这香甜,是往后几十年里,任何精致点心都无法比拟的。
夜里,是属于炭火盆的。那是一口旧铜盆,底下架着红红的炭火,上面罩着一个竹编的、镂空花纹的烘罩。一家老小便都围拢过来。祖母总是坐在那张旧的藤椅里,就着火光,慢悠悠地做着针线。火光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跳跃,明一阵,暗一阵,像一首无声的、古老的诗。母亲则会变戏法似的,从火盆的热灰里,给我们煨上几只红薯,或是一把黄豆。红薯的焦香,豆子爆开的“毕剥”声,是和着屋外呼啸的风声一同进行的。那风在门外徘徊,愈加显得屋内的这一方天地,是何等的安全与温暖。我们蜷在矮凳上,听着大人们讲那些古老的、不知传了多少代的故事,神仙鬼怪,才子佳人,一切都混在暖洋洋的空气里,催得人昏昏欲睡。这份因抵御外寒而凝聚起来的家庭的亲密,是那样地朴素,又那样地牢不可破。
雪,在南国是极难得的恩赏。若有一年,早晨推开窗,看见世界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、怯生生的白,那便是天大的惊喜了。我们会在雪地里发疯似地奔跑,尖叫,用通红的小手,去接那一片片凉沁沁的、六角形的琼花。虽然那雪薄得积不起来,更堆不成雪人,但只是看着屋顶的黑瓦镶上了一圈白边,看着光秃的树枝上托着一点点积雪,便觉得心满意足,仿佛整个冬天,都因此而圆满了。
这些记忆里的暖,是具体的,有形状,有气味,有声音。它们是捶打年糕的号子,是炭火盆的毕剥,是烤红薯的焦香,是薄雪落在掌心的微凉。它们是困顿中的慰藉,是清贫里的丰饶。如今,暖气充足的房间里四季如春,琳琅满目的零食唾手可得,那份因“等待”与“稀缺”而显得格外珍贵的喜悦,却再也找不回来了。童年冬日的暖,暖在人情,暖在期待,暖在那份与自然节律紧紧相依的、朴素的生命力里。
于是,这景与忆,便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,将我这样漂泊在外的游子,密密地罩住了。这愁,是双重的。
一层是空间上的。离了那湿润清寒的天地,离了那炭火与年糕的人间烟火,我便像一个失了根系的浮萍,在这座庞大而喧嚣的北方都市里漫无目的地漂着。这里的冬天,干冷、暴烈,风像一把巨大的、无形的扫帚,将街道扫荡得干干净净,不留一丝温情。人与人摩肩接踵,心与心却隔着重山。电梯里,地铁上,尽是沉默的、疲惫的面孔,眼睛盯着发光的手机屏幕,仿佛那里面有一个比现实更值得栖息的世界。每当华灯初上,看着那高楼里透出的、成千上万的、格式化的窗光,却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的,那种无边的寂寞,便如这北方的寒气一般,透彻心肺。我时常在梦中回到那片雾蒙蒙的、湿漉漉的天地,醒来时,枕边却是一片冰凉的湿意,不知是泪,还是那梦中故乡的雾气所凝。
另一层,却是时间上的。即便我真的回去了,那个记忆里的故乡,恐怕也早已面目全非。泥泞的田埂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,老屋被拆了,建起了贴着白瓷砖的小楼。河水许是污浊了,那片可以划薄冰的溪滩,也许早已填平。更可怕的,是人情的流变。童年的伙伴,早已散落四方,或在更远的异乡,或在琐碎的生活里消磨了旧日的容颜。即便相逢,除了追忆几句模糊的往事,还能说些什么呢?我们各自的人生轨迹,已如两条交叉而过的线,愈行愈远了。
这种“回不去”的怅惘,比单纯的“不在场”更令人感到无力。我们这一代人,被时代的洪流推着,争先恐后地离开家乡,奔向代表着“发展”与“机会”的都市。我们获得了物质上的某种满足,却付出了精神上流离失所的代价。身体在繁华里奔走,灵魂却始终在寻找那片失落的水土。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宿命:成了故乡的客人,也成了都市的异乡人。
社会的发展,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,载着我们的身体飞奔,却常常将一些珍贵的情愫,遗落在了身后的站台上。故乡冬日所象征的那种情感结构,正在无可挽回地发生着变化。
首先是乡情的稀释。过去的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,是基于共同的生活经验与文化背景。那时的“乡”,是一个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、稳固的共同体。而今,村庄空心化了,熟人社会在解体。年轻一代对土地的依赖与感情已极其淡薄,他们的乡愁,或许更多是对于童年的一种抽象怀念,而非对那片具体水土的眷恋。乡情,从一种血脉里的本能,渐渐变成了一种可供展示的、文化的符号。
其次是友情的格式化。童年的友情,是在田野里、在溪畔、在共同参与的年糕香气里“长”出来的,它粗糙,却结实。如今的友谊,许多则是在职场、在酒桌、在一次次利益往来中“建”起来的,它精致,却也脆弱。我们有了无数的“朋友圈”,却难得有几个可以深夜畅谈的知己。交流的工具前所未有的发达,心灵的壁垒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厚重。
再者是爱情的加速与物化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,马,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那种在冬日炉火旁慢慢滋长的情愫,带着羞涩与试探,有如冰雪下的春芽,过程本身便是一种醇厚的享受。如今,一切都讲求效率,“闪婚”、“速食爱情”大行其道。爱情这杯需要文火慢炖的酒,被置入了快节奏的离心机中,情感的沉淀变得困难,维系一段长久的关系,需要对抗的外部诱惑与内部倦怠,都比以往要多得多。
最后,是亲情的远距化。从前,一家人在冬日里围着炭火盆,是日常。空间上的邻近,自然促成了情感的亲密。而今,子女在大城市,父母留守故乡,成了常态。视频通话固然便捷,却终究隔着一层冰冷的屏幕。那种可以触摸到的温度,可以随时递上的一杯热茶,可以无言对坐的默契,是任何技术都无法完全复制的。亲情,在空间的拉扯中,不得不学会一种新的、更为坚韧却也更为辛酸的维系方式。
这些变化,悄然而深刻。它们不是任何人的错,而是社会发展与精神演进不同步的必然结果。我们的物质文明飞速前进,高楼拔地起,网络通全球,但我们的情感模式、伦理观念与精神家园的建设,却未能以同样的速度完成现代化的转型。我们拥有了更丰富的物质,内心却可能感到更为饥渴;我们联系得更方便,孤独感却可能更加深重。这就像一个人,一条腿已经迈入了信息时代的门槛,另一条腿却还深深地陷在农业社会的泥土里,姿态不免别扭,内心不免撕裂。
然而,人终究是需要一点慰藉的。在这巨大的变迁与疏离中,我总在试图寻找那些残存的、可以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信物。
偶尔,在北方冬日的超市里,看到冰柜中出售的机制年糕,整齐,雪白,毫无瑕疵。我会买一块回家,或炒或煮,然而,任是加上再多的糖,再鲜的汤,也吃不出童年那股子带着号子声与热气的美味了。那失去的,不是味道,是整个氛围,是那套完整的情感与文化仪式。
前年回乡,已是腊月二十八。街市上熙熙攘攘,尽是置办年货的人,现代化的包装琳琅满目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,忽然在一条老街的转角,闻到一股熟悉的、焦甜的香气。是一个老人,推着旧式的铁皮炉车,在卖烤红薯。我买了一个,捧在手里,那滚烫的温度,透过粗糙的薯皮,一丝丝地传到掌心,竟让我有片刻的恍惚。我站在那街角,不顾体面地、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那一刻,仿佛时光倒流,我又变成了那个围着炭火盆、眼巴巴等着红薯熟透的孩子。
这微不足道的瞬间,于我,却是一次小小的心灵救赎。它让我明白,故乡的冬日,或许已不是一个地理的存在,而是一种精神的向往,一种情感的底色。那些具体的事物在消逝,但那种对于温暖的渴望,对于团聚的期盼,对于生命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感知,却并未泯灭。
窗外的北风依旧,楼宇的灯光依旧。我缩回思绪,将那本旧相册合上。故乡的冬日,终究是渐行渐远了。它像一幅褪了色的画,只剩下些许模糊的轮廓与依稀的韵味,供我在这样一个又一个异乡的清夜里,反复摩挲,独自品味。
那清寒的雾,那温暖的炭火,那香甜的年糕,那薄脆的冰,还有那早已散落在天涯的亲人与伙伴……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生命底层那一片永恒的、湿润的、清冷的,却又无比温暖的冬天。这冬天,不在日历上,而在我的心里,下着一场永不停歇的、温柔的雪。
查看更多>>上一篇:夜读散文|《暖冬》 下一篇:晨读散文|初冬暖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