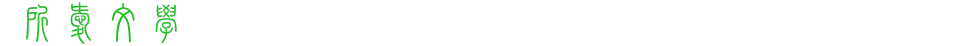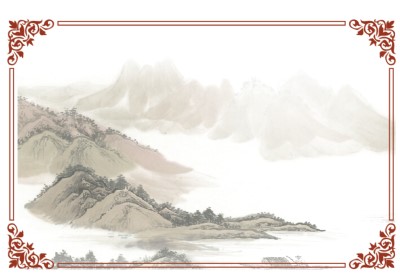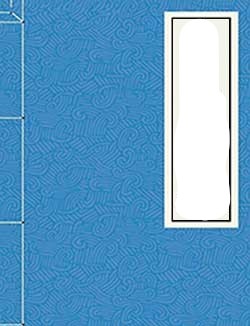首页 >抒情散文 >散文 | 故乡的胡同
散文 | 故乡的胡同
2025-05-21 12:40 编辑:云彩间

陕北的胡同从不是笔直的,它们像老人手上的青筋,曲曲折折地爬在黄土坡上。我家的窑洞就在第三条胡同的尽头,门前有盘老石磨,每天天不亮就响起"吱呀——吱呀"的呻吟。母亲总穿着靛蓝布衫推磨,玉米粒从磨眼漏下去,变成金粉从磨缝溢出来,落在她补了又补的围裙上。
那年腊月,石磨突然裂了道缝。父亲蹲在磨盘边抽了三袋旱烟,第二天背着褡裢去了三十里外的石匠铺。回来时他棉袄结着冰碴,肩上却扛着新凿的磨盘。月光下,我看见他冻裂的手掌粘着石屑,血珠凝成暗红的玛瑙。如今那盘磨早就不用了,可每当我在城市超市看见精装面粉,耳畔总会响起那年冬天父亲凿石的"叮当"声。
胡同中央有棵老枣树,树干上刻满歪歪扭扭的"正"字。放羊的老汉说,这是光绪年间他爷爷那辈人记工分用的。夏天里,树荫能罩住半个胡同,婆姨们端着针线笸箩坐在树根上纳鞋底。谁家汉子从煤矿回来,黑脸上只有眼白和牙是亮的,女人们就哄笑着把枣花插在他安全帽的裂缝里。
最难忘的是枣子熟透的时节,孩子们举着长竹竿打枣,红雨点似的落下来,砸在刘婶新晒的辣椒酱上。她抄起扫帚追我们,追到一半自己先笑了,撩起衣襟给我们兜枣:"碎崽子们,慢些吃,别噎着。"去年回乡,看见老枣树枯了半边,树下的石墩上坐着刷短视频的年轻人,再没人记得那些"正"字里埋着多少担小米的往事。
三爷爷的烟袋锅是胡同里的北斗星。冬夜里,男人们挤在他家窑洞炕上,看他把烟叶子按进铜烟锅,"滋啦"一声划亮火柴。那些关于收成、旱灾、公社旧事的对话,随着烟圈在油灯上方盘旋。有时说到动情处,他会用烟杆敲击炕沿,震得墙上年画里的胖娃娃簌簌掉金粉。
我离开家乡那年,三爷爷把烟袋杆塞进我行李缝:"娃娃,在外头难受了,就想想这烟锅子的味道。"后来在深圳出租屋里,当我第三次被客户退回方案时,突然闻到记忆里的旱烟味。打开窗才发现是对面工地民工在抽烟,那种劣质卷烟的气味,却让我对着夜色哭得失了声。
胡同里最金贵的是王叔家的水窖。干旱时节,女人们排队打水时的木桶碰撞声,比教堂钟声还神圣。有年大旱,我家分到的水只够煮半锅稀粥,母亲却舀出两瓢送给刚生完孩子的张家媳妇。半夜醒来,看见她正就着月光舔碗底最后一粒米,窑洞土墙上她的剪影,比我后来在美术馆看过的任何雕塑都美。
如今家家通了自来水,可老水窖还在。去年清明回去,看见窖台石缝里长出丛蒲公英,轻轻一吹,白絮飘过那些当年排队踩出的光滑凹痕,像时光留下的羽毛笔迹。
李家的瞎眼奶奶总坐在碾盘旁晒太阳。她说自己虽然看不见,但能听出每个邻居的脚步声:"张家小子左脚重右脚轻,赵家媳妇喜欢拖着布鞋走..."有次我故意踮着脚经过,她却笑起来:"碎猴儿,你喘气声像小风箱哩!"后来我在城市地铁里被人群推搡时,总会想起她那句话——原来真正的故乡,是连你的呼吸都认得的地方。
她去世那晚,全胡同人都来守灵。月光把碾盘照得发亮,恍然间仿佛看见老人又坐在那里,用盲眼"望"着星空。治丧的笙箫声里,不知谁说了句:"往后夜里路过这儿,再没人问'吃了没'了。"整个胡同突然安静得能听见露水凝结的声音。
去年胡同拆迁时,八十岁的父亲执意要回去捡半块磨盘。他蹲在废墟里,用树棍拨拉出我小时候玩的羊拐骨,已经风化得像是史前文物。当推土机轰鸣着逼近最后一座窑洞时,突然有只野鸽子从烟囱里飞出来,所有人都仰头看它掠过高压电线,消失在山峁后面。
现在我的书房里摆着从故乡带来的三样东西:半块磨盘、装旱烟的葫芦、还有用胡同老枣树木雕的笔筒。每当加班到凌晨,摸着笔筒上粗糙的木纹,就仿佛又听见枣子落地的"啪啪"声,看见母亲站在窑洞前用手掌搭凉棚的模样。这才明白,所谓乡愁,不过是所有远去的事物,都在血液里长出新的根系
查看更多>>
上一篇:夜读散文 | 荷尖悬玉露,... 下一篇:夜读散文|一天,一年,一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