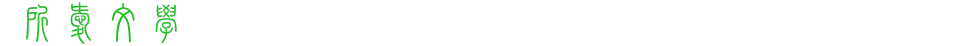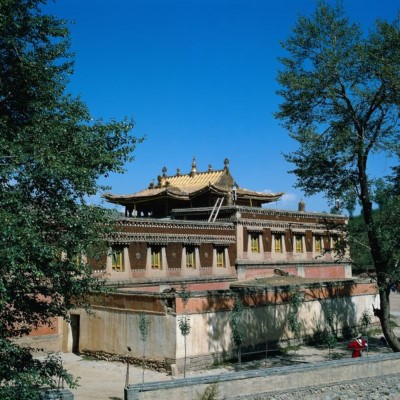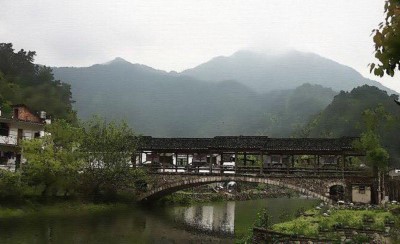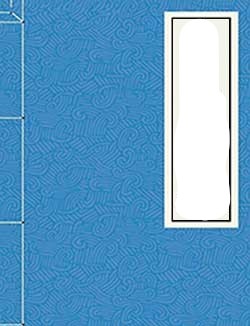晨读散文 | 中年人生,求缺不求满
2025-05-21 12:48 编辑:云彩间

麦田此时最有看头。穗子灌浆将满未满,籽粒隔着青皮能掐出浆水,却还没到低头垂首的时节。农人背着喷雾器在地头转悠,指尖捻开麦穗察看,脸上既无焦虑也无狂喜。他们懂得:此刻的"未满"恰是最好的状态——若籽粒太实,反倒怕来场暴雨折了腰杆;若浆水不足,又恐旱风抽干了元气。
菜畦里的黄瓜纽子顶着黄花,辣椒苗刚结出灯笼状的青果。这些活物都在演绎着"小满"的哲学:辣椒若太早红透容易烂秧,黄瓜长老了便生苦味。母亲在世时常说:"看菜园子要赶早,迟了就只能收老梆子。"现在想来,这话里藏着多少生命的玄机。
河滩上的芦苇正抽新叶,青翠的苇尖刺破水面,却始终留着三寸空隙。野鸭在苇丛间游弋,身后拖出的水纹很快被水流抚平。自然界处处透着"不可太满"的智慧:河水涨到七分便要退,花朵开到八成最好看,月亮将圆未圆时最耐寻味。
前日遇见老同学志明,他刚辞去银行副行长职务。"每天批贷款看到数字就恶心",他在羊肉泡馍馆里掰着馍,动作比二十年前在宿舍泡方便面时还认真。馍块在碗里载浮载沉,像他这些年的际遇。我想起小满时节的麦穗——志明现在就是棵恰到好处的麦子,浆水饱满却尚未被职务压弯脊梁。
妻子整理旧物,翻出我三十岁时的笔记本。泛黄的纸页上写着"五年内要完成三部长篇",字迹力透纸背。如今二十年过去,这个目标就像小满后的麦地——有的穗子被鸟啄了,有的遭了霉病,但终究收了几袋实实在在的粮食。中年人回头看年轻时的誓言,就像老农看自己清明时播下的种子,既要接受歉收的垄沟,也要珍视意外的丰稠。
女儿在视频里展示她的插花作品,刻意在青瓷瓶左侧留出空白。"老师说要留'呼吸的空间'。"她转动屏幕时,我看见她公寓墙上挂着的书法——"知白守黑"。这四个字突然击中了我:中年何尝不是在经营一幅留白的人生卷轴?那些未实现的抱负、半途而废的计划、求而不得的情谊,都是画面上必要的空白。
终南山下的果园主人老周有套理论:"果子七八分熟时摘,放两天刚好;若等树上熟透,运到市场就烂了。"他粗糙的手指抚过桃子的绒毛,动作轻柔得像对待婴儿。这让我想起写作——文章写到七分时搁笔,留给读者想象余地;若把话说尽,反倒失了韵味。
昨夜暴雨突至,今晨去查看巷口的石榴树。那些前天还骄傲昂首的花苞,经过雨水冲刷反而开得更从容。有些花苞始终紧闭,倒比盛开的更显精神。这景象颇似中年心境:年轻时急着绽放所有才华,如今懂得含而不露也是境界。就像小满时节的蚕豆,鼓胀的豆荚里总留着几粒瘪子,农人却不以为憾——有缺憾才是常态。
茶馆里遇见退休的周老师,他正用毛笔在报纸边练字。"写坏了就团掉,反而比年轻时战战兢兢写得自在。"墨汁在新闻纸上晕开,像极了人生计划外的变故。我们相对而笑,各自碗里的茶都只斟七分满——这是老茶客的默契,留出闻香的空间,也给意外话题腾挪余地。
麦收前的这段日子,农人反而清闲。他们蹲在地头抽烟,看云识天气的古老智慧写在皱纹里。不像年轻人时刻盯着手机里的天气预报,这些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,更相信"天有天的安排"。这种从容,源自对"不满"的接纳——旱涝本是常事,关键在于留足应对变故的余力。
我的书桌抽屉里躺着半部未完成的小说稿,纸角已经卷边。曾经为此焦虑失眠,现在却觉出它的好处——就像留着的麦种,给未来存个念想。小满时节走在田间,会发现最饱满的麦穗往往微微低头,它们懂得"满招损"的古训。人生行至中年,那些未竟之事、未圆之梦,何尝不是命运慈悲的留白?
傍晚散步,看见广场上跳交谊舞的中年夫妇。他们的舞步说不上标准,但那份怡然自得,恰似小满时节的万物——不再急着生长,也尚未走向衰颓。女人鬓角的白发在夕阳下闪着银光,男人皮鞋的折痕里积着灰尘,他们旋转时在地面划出的圆弧,永远差三十度才满。
槐花的香气突然浓起来,提醒我小满之后便是芒种。生命就是这样环环相扣的节气,每个阶段都有其"恰好"的刻度。站在五月的尾巴上,我忽然明白:中年之美,正在于懂得像对待小满的麦田那样对待自己——留些浆水不灌满,存些力气不耗尽,在将满未满之间,活出生命的余味悠长。查看更多>>
上一篇:散文原创 | 南浔诗画里的... 下一篇:笔墨祭 余秋雨散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