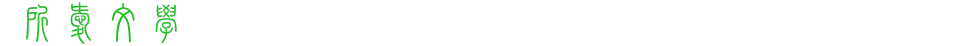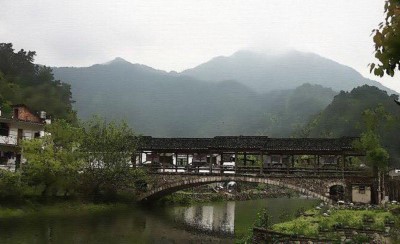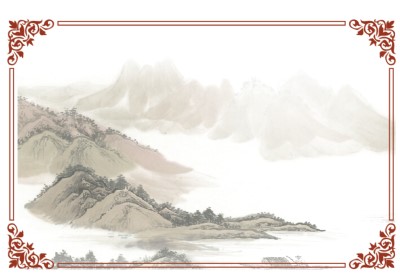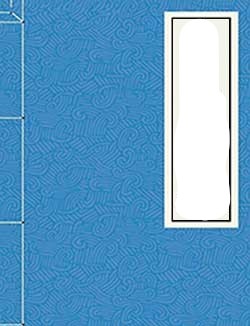首页 >散文赏析 >夜读散文|春归梦里人
夜读散文|春归梦里人
2025-02-21 11:53 编辑:云彩间

文:洛少华
每年春节归乡,我都会独自在堂屋的榫卯柜台前长久伫立。槐木相框里,祖母的银发被岁月镀成霜色,目光却始终温润如初。唯有这时,那些沉睡在时光褶皱里的记忆才会如老屋冬日房檐下的冰棱,在暖阳里渐渐融化出往日湿漉漉的光影。在这个被时代的高速列车抛在身后的陕南小村落,平民的记忆如同后山溪涧,总在某个暗夜悄然漫过隐蔽幽深的心堤。1929年,祖母出生了——那是新纪元诞生的第八个年头,红色星火尚未燎原;1929年,距祖母与世长眠的2012年,隔着八十三载人世风霜。这位裹着小脚穿越两个世纪的妇人,掌纹里嵌着饥馑年代的草根,眼角堆着合作社时代的麦芒,却在生命最后的春天,用皲裂的掌心焐热过我高考那年的准考证。黄山…“村”,方寸汉字之差,便是两重天地。若再缀上行政前缀,更成云泥之别。秦岭深处,转山转水,世事迁移。当年村西头的老磨盘如今已停转,裂纹里栖着几代人的叹息;曾独卧牛棚门槛的瘸腿黄牛,皮毛上染过几度风雨几成暮色。当高科技卫星定位将故土凝成冰冷的几个楷体字,那些散落在等高线间的前尘往事,便化作游子脐带里永不干涸无法撕下的血痂。
祖母那个沾着乡间晨露的土气名字,在灶膛火星与裹脚布里倔强生长。她的生辰八字浸着旧时代的苦艾:首段姻缘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缔结,四个稚儿在土改丈量土地的皮尺间降生。当新中国的晨钟撞碎阴沉山雾,她的蓝布围裙兜着合作社的新生麦种,却也在某个寒露夜,独自舀尽门前池塘里的清冷月光,浇灌亡夫的枯冢。祖母人生的第二春伴着入赘的锣鼓而来。闯关中的中年麦客的宽肩扛起九口之家的炊烟,却扛不动过继文书上晕开的泪渍。长子的姓氏随麦粒撒落渭西平原,幼子的乳名在张姓族谱里生根。祠堂香案见证着这个奇异的家族图谱:李王张三姓的枝桠共生于同一株苦楝,每逢年关,异姓兄弟带回的关中风干馍与陕南核桃饼,在供桌上氤氲出奇异的甜香。我童年的黄昏总在第二任祖父的竹梢与祖母的围裙间游荡。老人家的烧火棍能在三丈外精准击中偷柿子的顽童,而祖母的蓝布大襟永远藏着烤得焦脆的红薯——那是她省下的口粮,裹着灶灰的余温。直到某个蝉鸣撕扯的夏日傍晚,我偶然窥见这位钢铁般的妇人伏在堂屋神龛前,用围裙角轻拭槐木牌位,她的泪珠坠在"已故…"的描金字上,碎成八瓣月光。
及至舞象之年,稀薄的命运打破了我高考前夜的寂静。萦绕过祖母的刺鼻的消毒水气味至今萦绕我身心深处。那年在学校隔壁医院康复科病房的绿漆墙皮下,祖母枯枝般的手腕插着输液管,却执意将床头补充能量的葡萄糖液推至我手:"念书费脑子"。她终究是没有等到足以冲喜的录取通知书降临寒门,棺木前的长明灯便已将她一生的皱纹镀成唬人的金箔。下葬那日,阴阳先生摇响铜铃的刹那,山风突然卷起纸钱,在新坟的苦楝树上旋成一只只青鸟。而今又逢新春。屋外夜色如霜,屋内相框玻璃蒙着水汽,恍惚间竟像祖母在轻轻呵气。手机地图可以定位的"黄山村"在漫天烟火里闪烁,星空宛如巨大的走马灯。星空之下,黄土地上,自由穿梭的鸟雀必会为祖母衔去清晨的露水,苔痕斑驳的泉眼必会替她吟唱入夜的安魂曲。
上一篇:散文夜读|春信 下一篇:散文 | 素锦流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