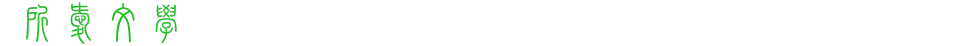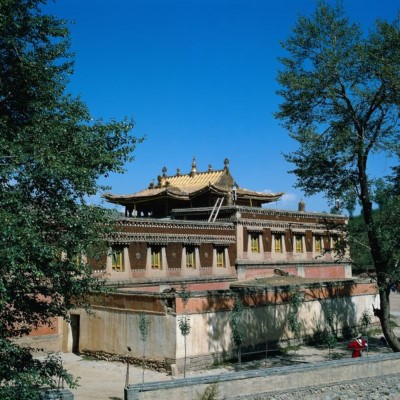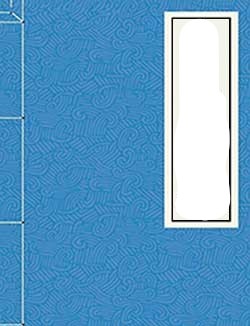首页 >文章 - 所爱文学-追寻心灵的艺术之旅 > 列表

- 2026-02-23 12:45夜读散文:年味烟花落尽,家的温暖是否犹在?异乡的伤痕可愈
当丙午年除夕的夜色,像一袭浸透了墨汁的绒布,缓缓覆上城市的轮廓,那些被准许在遥远角落绽开的、零星的烟花,便成了这绒布上匆匆绣上又旋即拆线的金线。它们升腾、迸裂、消散,传来的声响经过楼宇的层层过滤,落到耳中,已是闷闷的、旧梦回声似的钝响。我立在异乡高处的窗前,掌心贴着微凉的玻璃,杯中的茶早已失却了氤氲的热气。忽然觉得,那片刻的绚烂,并非欢庆,倒像一声集体无意识的、悠长的叹息——为又一段被折叠、被快递...

- 2026-02-23 12:43夜读散文 : 越到过年,越是明白家永远是心灵的码头
窗外是城市夜晚不灭的灯火,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闷响,不是爆竹,许是哪个顽童扔了颗摔炮。日历一页页撕得薄了,年关便像一层看不见的、却越来越浓的雾,悄无声息地漫上来,裹住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。空气里仿佛也浸透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,不是商场里循环播放的喜庆乐曲,也不是街边挂起的红灯笼,而是一种更沉、更静的东西,从记忆的深处,从骨血的缝隙里,丝丝缕缕地渗出来。人到了这个年纪,忽然就懂了,越到过年,心里那根...

- 2026-02-23 12:41夜读散文:散文里的年味
没有鞭炮,没有锣鼓。但我心中却依次响起了老舍笔下的轰鸣,走过了沈从文灯影中的山道,掠过了鲁迅审视的冷眼,回到了冰心笔下母亲的厨房,重现了丰子恺画中的童戏,最后,试着找回一点朱自清文中那孩子般的、对新年的清澈期待。这交织的旋律与画面,便是我所品嚐到的、复杂而丰厚的“年味”。它由文字传承,由记忆酿造,最终在每一个认真生活、认真感受的当下,被重新唤醒,获得属于这个时代的气息与形状。

- 2026-02-23 12:39晨读散文:阳光,春日里的精灵
这春日的阳光,究竟是从何时开始,不再像冬末那般苍白乏力,而是变得有了重量,有了温度,有了声音,甚至有了性灵的呢?我说不清。只觉得它像一位久别重逢的故友,又像一位初次造访便毫不认生的精灵,在某一个清晨,不请自来,轻轻地、却又无比确凿地,落在了我的阳台上。我于是便倚着这冰凉的栏杆,将自己全然交付给这个早晨,交付给这位名唤“阳光”的春日精灵了。它首先拂过我的面颊,那触感是极细腻的,仿佛最上等的江南丝绸,...

- 2026-01-31 20:44夜读散文 | 最是人间烟火色,足慰半生风霜路
华灯初上时,北风便紧了起来。那风是带着哨子的,尖利地掠过枯枝,卷起地上薄薄的积雪,在空中旋成一片迷茫的雾。我拢了拢衣领,呵出一口白气,看它在昏黄的路灯光里迅速消散,融入这无边无际的、簌簌落下的雪霰之中。世界仿佛被一层细密的、无声的纱笼罩了,远处的楼宇、近处的树影,都只剩下朦胧的轮廓,像一幅洇了水渍的旧水墨。唯有那雪,是不紧不慢的,一片,又一片,悠然自得,带着一种近乎神性的、覆盖一切的耐心。它们从不...

- 2026-01-31 20:41夜读散文|母亲是一种岁月
文/毛根强 童年时,母亲便是整个世界。那世界小巧而温热,恰好能容我蜷在她用臂弯圈成的暖巢,隔绝风雨,盛满柔暖。春雨淅沥的清晨,她总撑着油纸伞来接我,伞面固执地偏向我这边——我周身干爽,她的半边肩膀却浸在冷雨里,洇开深色的湿痕,我缩在她身侧,看水珠沿伞串成细碎水帘,她掌心覆在我肩头,暖意顺着衣料纹路漫开,将潮润空气里的雨腥气烘得绵柔。炊烟漫卷的黄昏,母亲是灶膛里跃动的温火,橘红光晕映着她额角细汗...

- 2026-01-31 20:39原创散文 | 最好的冬季在宋朝
文字/鑫垚 最近冷得连门都不想出了,东北的四九天,只有东北人才能体会得完全和透彻。我这里是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,再往北去,零下四十多度也是有的。刺骨的寒风也来凑热闹,刮到脸上像刀割一般疼痛,还极擅长拐弯,偏要往人的衣领里钻,不弄得你透心凉决不罢休。雪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,市政部门派了铲车、在道路上撒了盐,仍是清不完、化不净,一眼望去还是白茫茫的一片。 临近年关,今天早上刚刚去外公的坟前拜...

- 2026-01-31 20:38晨读散文 | 腊八过后就是年
腊八的余韵,还粘在瓷碗壁上一圈淡淡的、米油凝成的白痕,像冬日呵出的一口气,还没来得及消散,母亲电话里的声音,便带着那股熟悉的、穿越千里仍旧温热的灶火气,熨帖又沉甸甸地覆上心头。 “今儿是孩子生日,别忘了。”她总是记得比我牢。声音里漾开的笑意,能让人立刻想见她眼角细密堆起的、阳光晒过似的纹路。随即,那笑意便像投入深潭的石子,漾开一圈更悠长的涟漪:“腊八一过,年就又撵到脚跟后头啦。今年……车子票好买...

- 2026-01-31 20:36散文|小生活中的小味道
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初学写作文,有些同学实在学不会,写得不成样子,老师会告诉我们,那就先把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用大白话罗列在一起,然后再慢慢练习修辞手法和细节描述。那么,如果将冬季、东北、凌晨这几个要素罗列在一起,又会给未曾经历过的人带来什么样的想像呢? 冬至过后,东北的冬天更像冬天了,一月份夜里的气温会跌至将近零下三十度,蔓延到天亮之前,黑暗加上严寒,这感觉,即便是亲身体验过的人,也很难描述得确...

- 2026-01-31 20:34夜读散文 | 雪覆大地,静待春生
雪是在昨夜悄然而至的,没有风声预告,也没有星辰送行,只是像一场沉默的约定,轻轻覆盖了这片沉睡的田野。清晨推开屋门时,世界已被一片无垠的洁白所接管,远山、近树、阡陌、沟渠,都失了棱角,融进这柔软而厚重的素净里。我踏雪而行,脚下的“咯吱”声是此刻天地间唯一的节奏,清晰又孤独,仿佛在丈量着冬日特有的寂静。这寂静并非空无,它饱满而丰盈,吸纳了秋日所有的喧嚣与丰饶,将它们沉淀在目光所不及的泥土深处。我漫步的...

- 2026-01-13 21:21夜读散文 | 一纸墨痕,半生回响
文:毛根强 书柜底层,一叠报纸静静躺着。纸页泛黄,边角卷起,像被时光反复摩挲过的旧地图。指尖拂过,油墨的淡香混着尘埃的气息,幽幽浮起。那些铅印的名字忽然撞进眼里,心猛地一颤,思绪倏地飘回八十年代。风里还带着那时的土腥味,混着广播匣子滋滋的电流声——那是我为县电台、报社写稿的岁月,清贫而滚烫。。 八十年代初的风,吹得人心松快。政策落地后,田埂上的脚步密了,晒谷场的笑声亮了,连山间的庄稼都挺直了...

- 2026-01-08 21:24夜读散文|冬天是诗歌般的季节
冬天,不是结束,而是另一首诗,更为磅礴的生命之诗,那不可或缺的、蓄势待发的、充满张力的序曲。它本身就是一首完整的、伟大的诗,值得我们用整个身心,去阅读,去聆听,去居住其中。

- 2026-01-08 21:22晨读散文 | 一场冬雪,一场静谧
我知道,明天,或者不久之后,这场雪会消融。它会化作冰凉的水,渗入大地,滋养沉睡的草根与虫卵。然后,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时刻,又以水汽的形式升腾,等待下一次的凝结与飘落。而世界,将在这一次次的覆盖与融化中,走向新的春天。人生,大抵也是如此。一场冬雪,一场静谧,一场于心魂深处悄然完成的、向更高处的甑选与抵达。

- 2026-01-08 21:20夜读散文 | 《冬韵荏苒,时光清浅》
当春风再度吹融最后的冰层,你会怀念这个冬天,怀念它给予的这份清醒的孤独、这份沉淀的安宁、这份在寂静中听清自己心跳的奢侈。因为你知道,这冬韵已沁入生命的年轮,那清浅的时光,也因此有了一抹永不冻结的、温润而坚韧的底色。

- 2026-01-02 19:46晨读散文|冬日处处寒,腊梅树树香
冬日,到底是来了。 不是那种“初肃”的、带着商量的、在秋的裙裾边徘徊的轻寒,而是真正的、不容分说的、君临天下的严冬。这寒,是彻骨的,仿佛并非从外界袭来,而是先从人的骨髓深处幽幽地渗出,再与天地间的冷气里应外合,将人里外三层冻成一个透亮的、动弹不得的冰壳子。它又是湿寒的,不像北方的干冷那般爽利、有刀锋的明快;这寒里氤氲着水汽,沉甸甸的,像浸透了冷水的旧棉絮,一层层裹挟上来,贴着你的皮肤,钻进你的关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