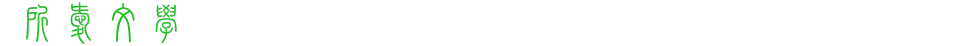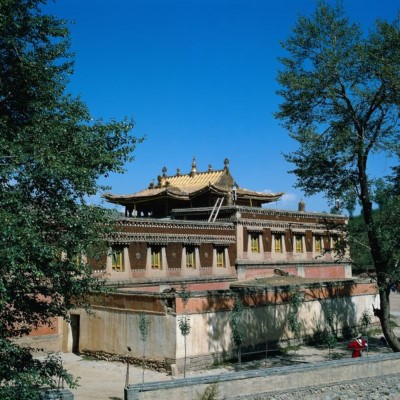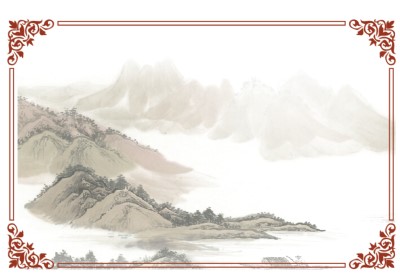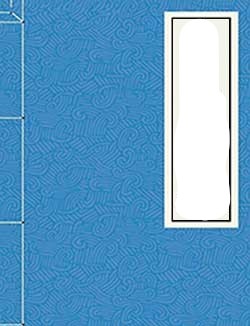首页 >文章 - 所爱文学-追寻心灵的艺术之旅 > 列表

- 2025-11-22 08:07晨读散文|初冬暖阳
这南国的初冬,终究是来得迟疑而温吞的,仿佛一位矜持的客人,在门外逡巡良久,才肯施施然探进半个身子来。节气虽已过了立冬,四下里却并无多少凛冽的肃杀之气,只是那风里,终究是挟带了些许清冽的、不同于秋日的凉意,像一块浸过井水的软绸子,不经意间拂上面颊,教人蓦地一惊,才省起冬的序章已然悄无声息地揭开了。然而目光所及,却依旧是那铺天盖地、几乎有些执拗的绿。这绿,不像春日那般嫩得逼人,也不似盛夏那样浓得化不开...

- 2025-11-17 20:36夜读散文 | 故乡的冬日
我总以为,冬天的魂,在南方是另一样的。它不似北国那样,用铺天盖地的雪,用凛冽如刀的风,来宣示自己的主权。南方的冬,是矜持的,是内向的。它来得悄无声息,像一滴极浓的墨,滴入清水中,不急于散开,只是那么幽幽地、缓缓地,晕染出一片洇润而清冷的底子来。这底子,便是我记忆中故乡的冬日了。 离家愈久,这景致在脑中便愈发清晰,带着一种潮湿的、拂之不去的凉意。 清晨常常是从一场弥天的大雾开始的。那雾不是一缕一缕...

- 2025-11-17 20:34夜读散文|《暖冬》
西安的午后,总是慢的。我踱上城墙,脚下的青砖被稀薄的日光晒出些许暖意,像是老人手心里攥久了的一塊溫玉。今年的冬,確是不同了。护城河的水并未完全封住,风过时,能听见冰碴子与流水私语的碎响,泠泠的,不那么刺耳。回民街那头,白蒙蒙的蒸汽扶摇而上,羊肉的膻香、甑糕的甜糯,全都搅在這片暖霧裡,將三九寒天熏得一派慈眉善目。這光,是斜斜地打过来的,没什么力气,却足夠將人的影子拉得老長,仿佛時間也跟著變得慵懶而寬...

- 2025-11-17 20:33晨读散文 | 立冬过后就是冬
节气更迭,天地悄然换装,寒风从北方的旷野席卷而来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凛冽,拂过城市的高楼和乡间的田野。清晨,我推开窗,一股冷空气扑面而来,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,像是冬日随手画下的抽象图案,晶莹剔透,却又透着寒意。街头的梧桐树,叶子已凋零大半,残存的几片枯黄在枝头颤抖,仿佛在诉说夏日的繁华与秋日的绚烂都已逝去。行人匆匆,裹紧了外套,围巾在风中飘扬,他们的脚步比往常更急促,似乎想尽快逃离这突如其...

- 2025-11-17 20:31晨读散文 | 深秋琐忆
那年深秋的冷风与今日一般无二,它从北方的山峦迢递而来,穿过城市纵横的街巷,最终停驻在我的窗棂。我记得那个清晨,推开门便见满庭银杏如金箔缀枝,风过时簌簌摇落,仿佛天地正举行一场庄严的告别礼。枫树却燃着赤红的火焰,一簇簇灼灼欲焚,与银杏的明黄交织成油画般的浓烈;而水畔的芦花已胜雪般飘摇,绒絮轻扬,似欲挽住流云的衣角。落叶的姿态最是耐人寻味:有的决绝如蝶舞,翩然坠地;有的踟蹰如倦客,在林梢盘桓再三,终是...

- 2025-11-17 20:29夜读散文|故乡的秋色
深秋的故乡,总是先从水汽里透出消息来。住在湘江支流边的这些日子,推窗便见河面上浮着薄纱般的晨雾,岸边的乌桕树已是半树赭红半树金黄,叶片上凝着细细的白霜,在初阳里闪着碎银子似的光。对岸的田畴里,晚稻早收尽了,留下齐整整的稻茬,像大地上刻写的密码。偶尔有白鹭掠过这片空旷,长腿在灰绿的水田里划过淡淡的痕,旋即又被寂静吞没。这般景致,总教人无端想起韦应物“故园渺何处,归思方悠哉”的句子来,可我的故乡,分明...

- 2025-10-11 22:04散文原创 | 《岭南无春,徽州有艾:一个游子的味觉乡愁》
文/迢迢去未停 身在岭南,漫长的夏天把秋冬扁扁地挤在来年春季里,而春又承接早早候着的夏。于是树在眨眼间黄叶落尽、嫩芽萌发、浓枝疯长;人常常是“今穿皮袄明穿纱”,一周把四季疾疾历遍,对于天气、穿衣、景观等等实在摸不着头脑。这样任性又短命的春天总让人的春日情结飘飘然飞回徽州——那是一个诗词书画都无法全力描绘的美丽春城。 清明来临,是艾叶最先埋下伏笔。那些鲜嫩油绿的枝叶呦,怎么能如此可爱,水霖霖、雾...

- 2025-10-11 22:02夜读散文|纸页间的秋声
秋声渐起时,书页便开始低语。 这是十月特有的私密对话——当第一片梧桐叶擦过窗棂,当暮色里的蟋蟀将月光纺成银弦,那些沉睡在纸页间的铅字便纷纷苏醒。它们先是窸窸窣窣地抖落灰尘,继而随着晚风翻动的节奏,在台灯的光晕里跳起圆舞。此刻若推开半扇木窗,便能听见整个秋天正以声浪的形式漫进书房:远处山峦吞咽夕照的吞咽声,近处露珠坠入陶瓮的坠玉声,以及书架上那些尚未开封的精装本,在暖湿气流中微微膨胀的呼吸声。 欧...

- 2025-10-08 19:39夜读散文|你好,十月
十月是从桂花树上跌下来的。先是三两朵砸在卖糖炒栗子的铁锅沿上,后来整条街都泡在蜜罐里似的,连收废品老汉的三轮车辙印都带着甜腥气。我在银行自动取款机前排队,隔着玻璃看环卫工老徐扫落叶,他竹帚划过地砖的声响像给秋天打着拍子。那些金黄的银杏叶明明轻得能飘上楼顶,落地的动静却沉得像他腰间那串钥匙——据说挂着亡妻留下的指甲剪。长假第三天,景区索道排队的游客们裹着同款冲锋衣,远远望去如同一条正在褪皮的蛇。穿汉...

- 2025-10-08 19:37夜读散文|秋色归处是故乡
当城市的第一片梧桐叶擦过车窗时,我正在早高峰的车流里数秒等待红灯。那抹枯黄突然跌落在挡风玻璃上,像一封被邮差误投的家书,带着北方干燥的季风气息。忽然就想起老宅天井里那棵歪脖子枣树,此刻该是缀满红玛瑙般的果实了吧?母亲总在秋分后用长竹竿敲打枝桠,枣子噼里啪啦砸在青石板上,有几颗会滚到西厢房的门槛边,被晨露浸润得发亮。三十年过去,那声音依然会在某个失眠的深夜,穿过两千公里的钢筋水泥,精准地落在我耳膜上...

- 2025-10-08 19:36散文|秋天的奶茶,母亲的爱
> > > 文/赵小嘉< < < 说起奶茶的口味,小时候我喜欢喝桃香四溢,粉粉嫩嫩的水蜜桃。长大之后,我喜欢在茉莉清香与奶绿的绵密中,寻觅那抹隐约的春意。关于这段记忆,母亲是不可忽略的。我因为肢体不便,很少出门。跟好朋友单独逛街这件事情对于我而言,比较难实现。所以,我时不时就被秋散发出的阵阵悲凉淹没。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失落,母亲是知道的。虽然,她没有说出口。每次跟好朋友逛街,她都会给我买一杯水蜜桃口味...

- 2025-10-08 19:34夜读散文|今年秋天的枫叶好美
暮色像稀释的墨汁般在枫林间流淌时,他第一千零一次站在三岔路口的老邮筒前。这个生锈的绿色铁皮盒子,如今成了整座城市最后的实体邮筒,如同他们爱情最后的纪念碑。风掠过树梢的瞬间,整片枫林突然簌簌作响,那些垂死的红叶挣脱枝头的姿态,让他想起去年今日她旋转时扬起的裙摆——也是这般决绝的艳红。 他们总说五角枫最懂离人心事。此刻西天的残阳正把枫叶烧成半透明的玛瑙,每片叶脉里都流动着熔金般的光晕。这光线太过奢...

- 2025-10-08 19:33散文|不喜欢说话的父亲
只是我总在等华丽的排比句,却忘了倾听这种粗粝的语法。现在他耳背得厉害,我得趴在肩上吼才能交流。但当我们合力抬起最后一块基石时,他手背在我腕上短暂地蹭了蹭,温度透过两层皲裂的皮肤传来,像三十年前那个雪夜,他把我冻僵的脚丫子按在自己肚皮上取暖。

- 2025-10-08 19:31夜读散文|中秋月又圆
月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圆的?或许是从母亲掀开蒸笼的那一刻。白雾裹着桂花香扑向窗棂,将八仙桌上的月饼映得油亮。父亲总在这时候摘下老花镜,把黄历翻得哗啦响:“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哩。”可我们哪里等得到十七?才过初十,小侄女就踮脚去够挂在门楣下的灯笼,红绸穗子扫过她翘起的嘴角,像要把整个秋天的甜都攒进酒窝里。 城市里的中秋是折叠的。办公楼玻璃幕墙倒映的月亮被压缩成惨白的光斑,外卖盒里躺着工业糖精调味...

- 2025-10-08 19:29原创散文|秋月如水
文字/黄汝兴 转身抬眸,已然秋天。 告别了炎热的盛夏,走进了清凉的秋天。 秋天的月亮,特别圆,特别亮,像水一样的柔美、清凉。 吃过晚饭,收拾停当,在四楼庭院的小石桌旁置一把躺椅,手摇团扇,全身放松。在桌上放一个紫砂壶,倒入一小勺普洱茶,一注烫水,高抬就缓,不急不忙,待热气渐散,一个人低吟浅酌,慢慢地品味绿茶的清香与恬淡。缕缕茶香弥漫于小院,浸润于肺腑五脏。一缕凉风拂去夜晚前的燥热,身心...